 《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 1913~1923》,严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4.00元
《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 1913~1923》,严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4.00元
十八世纪率先在北美和西欧确立的“法治国”理念,包含着表里不同的两
可惜的是,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人(并非后来的中国国民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后者的前身)只强调“法治国”理念的表面,主张“宪法之目的,在束缚行政权,使为国会之役使,将一切威权给诸国会,使其为立法独尊。”虽然北洋派和一些拥护袁世凯的地方都督(包括后来护国反袁的蔡锷)、以及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都主张加强国家权力,但由于国民党人占据优势,首届国会在民国初年先后出台的《临时约法》和《天坛宪法草案》都规定立法权凌驾于行政、司法权之上,并对后者形成单向制约关系。当然,“国会和国民党表面上是提倡民权主义,实际上是希望借助未来宪政制度中立法权超过行政权的制度设计,以达到制约袁的权力、独揽国家大权的目的,完成1912年辛亥革命南方党人没有实现的权力目标”,(第205页)――其“会党”本性可谓昭然若揭。
不仅如此,“1913年的民国制宪工作是一种法国式的国会制宪模式。这种模式完全以国会为主导,排斥其他政治利益集团参与。它不同于美国式制宪会议模式的开放特色,存在严重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同上)“民国国会从讨论制宪模式开始,就不愿意与其他政治集团分享制宪权。在制宪过程中,更没有兴趣听取袁世凯政府关于制宪的意见……制宪会议的多数成员在二次革命后政治形势相当严峻时,也不愿意冷静地思考妥协的必要性,即使只是暂时的实质性妥协。”(第209~210页)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国民党人对北洋派等其他政治利益集团的排挤,自然逃不过对方的反扑。过去论者常常将袁世凯视为颠覆宪法秩序的罪魁祸首,实则“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事实表明,1913年制宪活动的结局是国会制宪会议与北洋政治集团一次策略互动的失败。袁在使用非法手段破坏制宪之前,已经尽其可能采用了一切合法的协商手段影响制宪进程。但是在激进派议员主导制宪会议的态势下,袁的政治企图惨遭失败。最后随着《天坛宪法草案》的完成,袁终于认识到温和的协商策略无法达到个人政治目的,这样威权专制与后来的君主立宪主义,就取代宪政民主政治,成为袁政治策略中的新宠,制宪进程因此而黯然中断。”(第216页)而在袁氏覆亡之后的1916、1917年,首届国会第一次复会期间,制宪进程本又绽露一线转机,但“由于当时的国民党系政团益友社全然不顾袁世凯死后地方军人力量崛起的政治现实,坚持立即实现以削弱地方实力派为目标的省制入宪,拒绝当时北洋政府与地方实力派在省制问题上的反对意见,最后致使省制问题流产,给予军人干预制宪的借口,制宪进程再次失败。”(第291页)直到1923年,首届国会第二次复会,制宪派议员才和直系军人掌控的北京政府达成制度性和实质性的妥协,制定出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形式上完成了近代制宪过程。但在此前的1922年,孙中山已经在南方发动国民革命,认为“国会招牌已成废物,不足起国人之信仰,故国会之纯洁分子,如能同来革命,则无不表示欢迎。”(第298页)――而此后蒋介石主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所推行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训政”制度,则又充分说明:一旦抛弃了“法治国”的理念,一个强大到了足以保护每一个人的国家,也就强大到了足以压迫每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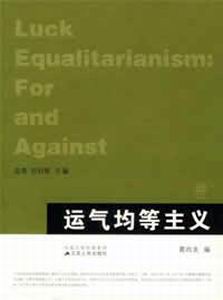 《运气均等主义》,葛四友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32.00元
《运气均等主义》,葛四友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32.00元
所谓“运气均等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平等观念:平等在于消除一切运气的影响。这里的“运气”(luck)泛指一切存在于个人选择和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包括“生来具有很差的自然禀赋、坏的双亲、令人不悦的个性、从意外与疾病中受苦等等”(第228页)。这种观念在古人看来未免渎神,因为在所有的宗教和神话语境里,运气都绝非纯粹的偶然性,而是某种神秘的秩序、力量或意志的产物,换言之属于适用于因果解释,而非概率解释的范畴。然而,自从休谟站在经验论立场上否定因果关系,将其重新表述为仅仅是“固定的关联、时空的邻近以及时间上的居先”以来,因果解释即使在科学领域中也是节节败退,现代社会科学更是普遍使用概率来解释因果关系,对运气问题似乎也就理所当然地确立了概率解释的合法性。加上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念很难接受个人对其选择和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负责任,因此,主张一种消除一切运气影响的平等观念,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从学理上讲,运气均等主义可以追溯到罗尔斯在《正义论》里提出的关于社会正义的“无知之幕”假设,这一假设旨在“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损”。但罗尔斯并未明确界定他所说的“机遇”和“偶然因素”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只有在如前所述的对运气问题的概率解释基础上,才能由“无知之幕”推导出运气均等主义。
然而,一旦顺着运气均等主义的理路走下去,就免不了遭遇悖论。不妨摘录本书编者对这一理路的论述:“当所有人都不受到运气的影响时,那么相当于说,我们要抵消一切运气因素的影响。我们先来看这个观点实际蕴含着什么。首先,我们将这种抵消理解为消除。但是,这就要求我们无所不能,能够随意地改变身边的一切事情……但除了上帝外,我们凡人肯定无法做到这点,因此必然有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即运气)要对我们的生活起作用,只在于是以哪种方式起作用,谁来承担这种作用的后果……因此,除非我们打算否认个人责任,否则我们就不能将不受到运气的影响视为个人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这样我们转向对抵消的另一种理解。第二,抵消不是消除,而是大家共担运气的影响,实际上就是运气的影响属于集体责任。一方面,这承认了我们在承受运气的影响时,能够承担个人责任,也就是说不受到运气的影响并不是我们承担个人责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我们必然要受到运气的影响,那么我们每个人必须承担相同的运气影响。这里集体责任就转变成了让每个人均担不可避免的运气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为他们的选择承担后果才是合理的,才是道德上可辩护的。”(第315页)――这里的悖论在于,为了“让每个人均担不可避免的运气的影响”,就必须假定“运气”在某种意义上是可分配的,但这也意味着“运气”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因果解释而非概率解释,因此并非纯粹的“机遇”或“偶然因素”,不符合“无知之幕”的适用条件。本书编者也从伦理学的理路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运气均等主义是自我挫败的。”(见“编选说明”)
上述论证中提到的因果解释和概率解释的分歧与悖论,背后其实涉及到现代性问题的“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现代人当然不必盲从古人对运气的因果解释,但那类因果解释中所蕴含的某种非人类中心的立场却是不无借鉴价值的。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设计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好”社会,人们根本无须设想“运气均等主义”之类的概念;反过来说,“运气均等主义”的内在悖论也揭示出,设计(还不是建设)一个既是以人类为中心、同时又是“好”的社会是何等艰难乃至几乎不可能。
 《赛伯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荷〕穆尔著,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38.00元
《赛伯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荷〕穆尔著,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38.00元
互联网创造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正在渗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根据柏拉图以降的西方传统本体论,赛博空间作为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要低一个等级。从这种传统的本体论出发,难免会把它视为陷人类于“异化”绝境的洪水猛兽。本书则根据波普尔和帕里斯勒(Helmuth Plessner)的“三种世界”理论,为赛博空间的本体论地位提出了辩护:“第一种世界是物质客体及其物理属性的世界;第二种世界是人类意识的世界,由思想、动机、欲望、情感、记忆、梦幻等构成;第三种世界是文化的世界,由人类的精神产品构成,例如语言、伦理学、法律、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和社会体制等等。尽管这些产物皆源自人类的精神(第二种世界),但是却具有某种独立性和永恒性。在此层面,它们类似柏拉图的永恒的理式世界,超越昙花一现的物质世界。我们可以把由全世界电脑网络所拓展的赛博空间视为第三种世界的最新发展阶段,这种新空间比过去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尽管赛博空间还依赖像电脑和缆线之类的物体,但是它已经大大地超越了第一种世界。”(第55~56页)
波普尔的学说在国内知识界曾经有过一番普及,但帕里斯勒就知者寥寥了。其实,“这位长期处在同时代人马丁・海德格尔阴影笼罩下的德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在英语世界也是直到最近几年才受人重视。然而正是他在1928年问世的《有机体与人类的发展阶段》(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一书中提出的“离心定位”概念,“使我们能够对信息和传播技术,例如电子显现和虚拟现实获得更好的理解,远胜过我们原来从一种笛卡尔式的二元本体论那里所获得的目前关于技术的大多数诠释。”(第189页)所谓“定位”是指生命体和其自身的空间界限之间的关系,所谓“离心定位”是指人不仅“内在于他的身体(作为内部体验或灵魂),并同时作为特定视角外在于他的身体”,而植物“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都不存在一个中心”,动物则只能“内在于它的身体”。(第191页)
与海德格尔以时间为中心的“此在”概念相反,“离心定位”概念是从空间和共时性的维度把握人的存在。技术在帕氏的人类学中占据重要位置,用他自己的话说:“人试图逃逸他本性无法承受的偏离中心的状态,他想弥补他生命形式构成的不足。偏离中心和需求的弥补是同一回事。我们不应从心理学意义上或从作为主体的某物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语境中的‘需求’。它是某种在逻辑上优先于所有需求、驱动力、趋势或意愿的事物。在这种基本的需求或裸裎(nakedness)中我们发现了万事万物的动机,尤其是对人类而言,这种动机集中体现在对非真实(irrealis)的关注和人工方法的运用,这是技术人工制品和它所服务的文化的终极基础。”(第193页)――这和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贬抑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本书接着帕氏的话头引申说:“技术和文化不仅是――甚或在首要意义上不是――维系人类生存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本体论的必要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宣称人类从来就是赛博人,亦即:人类是由有机因素和技术因素双重构成的生物。”(同上)――由 此有望建立一种赛博空间的人类学。这种新型的人类学非常必要,因为,“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在技术的影响下,经历了某种基本的认识论转向。如果认为当今智人的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标志了人类进化的终点,则未免太天真了。”(第18页)
此有望建立一种赛博空间的人类学。这种新型的人类学非常必要,因为,“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在技术的影响下,经历了某种基本的认识论转向。如果认为当今智人的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标志了人类进化的终点,则未免太天真了。”(第18页)
《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美〕夏伊勒著,张若涵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2月版,47.00元
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早已脍炙人口,但就现场的真实感和细节的丰富性而言,这本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他在柏林担任记者期间的日记选萃无疑更胜一筹。它问世于美国尚未卷入战争的1941年7月,因此读者大可不必担心作者出于政治正确的后见 之明对原始材料做了手脚。作者对国际事务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敏锐的洞察力,无论对纳粹德国、西欧民主国家还是苏联都不抱幻想,然而又始终心怀正义必胜的信念,比同时代许多深陷意识形态泥潭的大知识分子要好很多。
之明对原始材料做了手脚。作者对国际事务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敏锐的洞察力,无论对纳粹德国、西欧民主国家还是苏联都不抱幻想,然而又始终心怀正义必胜的信念,比同时代许多深陷意识形态泥潭的大知识分子要好很多。
《茶叶之路》,〔美〕艾梅霞著,范蓓蕾、郭玮等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2月版,35.00元
从十七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从北京经蒙古至彼得堡的“茶叶之路”成为清、俄两大帝国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茶叶也长期成为欧亚大陆腹地的硬通货。本书全景式地描述了这条商业大动脉的兴衰史。不同于传统的中国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作者将重心置于茶叶之路的中间地段,探讨了茶叶贸易对蒙古草原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格局的塑造力量,以及蒙古民族在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